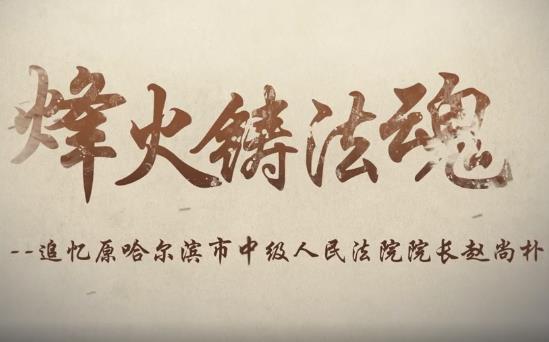8月18日一早,日頭剛把遼寧省海城市人民法院南臺人民法庭門前的臺階曬得微熱,門口那輛便民輪椅就已被擦得锃亮,輪軸上還帶著點新上的潤滑油。
沒過半小時,工作人員就小心翼翼地扶著一位老人坐了上去,輪子碾過無障礙通道的聲音,輕得像怕驚擾了誰。
這場景在基層法庭不算新鮮,卻藏著“如我在訴”最實在的理兒——把自己當成來辦事的老百姓就知道該往哪使勁。

法庭為老人提供輪椅接送暖心服務
從“怕麻煩”到“少跑腿”
細節里藏著貼心的秤
不久前張大爺來的時候,手里攥著份皺巴巴的合同,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。九旬的人了,腿腳不利索,說話都得喘兩口氣,卻一門心思要弄明白“這合同到底作不作數”。
法庭工作人員一看這情形,沒等老人開口問流程,先把輪椅推到了門口。“大爺,您別急,材料我來拿,咱今兒就在一樓說事,不用爬樓梯。”立案窗口的小姑娘一邊接過合同,一邊招呼同事準備老花鏡和溫水。連調解時間都特意選在下午兩點,“這時候您精神頭足,咱慢慢說。”
到了調解室才發現,細節想得更細:飲水機的出水口特意調矮了,急救藥箱就放在觸手可及的柜子上,連法官說話都放慢了語速。“您看這一條,就好比街坊借東西,寫明白啥時候還、咋還才算沒毛病。”法官指著合同條款,用老人聽得懂的話打比方,沒說一句“要約”“承諾”的詞兒。張大爺后來攥著調解書念叨:“原以為法院門檻高,沒想到比家里孩子想得還周到。”
不光是照顧老人,法庭里的適老設施常年備著:老花鏡度數換了好幾茬,就為了能對上不同老人的眼;飲水機旁總放著一次性紙杯,杯沿還特意磨過邊,怕刮著嘴。這些事說起來細碎,卻像桿秤,稱著司法服務離老百姓有多近。
從“吵翻天”到“握握手”
調解室里有解疙瘩的巧
今年4月下旬,南臺法庭和海城市司法局王石司法所聯合成立的“清風調解室”剛掛牌,就遇上了樁棘手事。
王石鎮東腰村的兩戶人家因為一把火燒雜草的事鬧到快動手——被告燒草引燃山火,把原告的果樹燒得焦黑,原告張口就要三萬賠償,被告卻覺得“頂多賠五千,樹本來就老了”。
第一次調解在村委會,兩邊吵得臉紅脖子粗。承辦法官成浩沒急著拍桌子,先往果園跑了三趟。“那幾棵蘋果樹,樹齡十五年,去年掛果大概八十斤,市場價一斤三塊五……”他拿著本子一筆筆算,連果樹后續三年的掛果損失都估得明明白白。
“都是一個村的,抬頭不見低頭見,真要鬧到鑒定、開庭,錢花了,情分也沒了。”說著把算好的賬攤開,“看看,按市場價算,損失大概一萬二,再扣掉老樹本身的折舊,八千塊是不是更合理?”旁邊村委會主任也幫腔:“都是種地人,不容易,退一步海闊天空。”
這話鉆進了雙方心里。沒半小時,被告紅著臉說:“我認,八千就八千,明天就把錢送來。”原告也松了口:“就按法官說的來,不為難街坊。”當天下午,賠償款就到了位,倆人頭天還瞪著眼,第二天就在村口握手嘮嗑。
成浩常說:“調解不是和稀泥,是把賬算清、把理說透,讓人心服口服。”這“清風調解室”就像個解疙瘩的巧匠,把村里的矛盾在萌芽里捋順了。
從“個案事”到“常態活”
司法服務往根上扎
有人說,基層法庭的故事,大多沒什么驚天動地,卻像毛細血管里的血,暖著最基層的肌理。
前文中張大爺的案子里,“涉老綠色通道”不是臨時起意,早就是法庭的固定流程:但凡遇上行動不便的當事人,輪椅、一樓調解室、適老設施全部“一鍵啟動”。而“清風調解室”也是南臺法庭和王石司法所琢磨了仨月的結果——村里的糾紛往往不是非得上法庭,找個信得過的地方把理說清比啥都強。
法官們常說:“法槌敲下去要響,可服務得沉下去才能接地氣。”這話不假,基層的法治從來不是冰冷的條文,是輪椅碾過臺階的輕響,是調解室里遞過去的一杯溫水,是把“你的事”當成“我的事”的那份實在。就像那輛總停在法庭門口的輪椅,輪軸轉著轉著,就把司法服務的轍印碾進了老百姓的心坎里。
夕陽西下時,南臺法庭的燈還亮著,有人在整理明天要帶進村的材料,有人在檢查輪椅的剎車。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瞬間,湊在一起,就是“司法為民”最生動的模樣——不用喊口號,老百姓心里自有桿秤。